热点推荐
- ·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北京常住人口1961
- ·家具厂因缺乏灭火设施起火燃烧5小时(
- ·北京28家老字号签责任书拒绝非法添加
- ·志愿者京哈高速截车救狗续:部分获救
- ·地税局干部受贿186万获刑10年半--中
- ·零点原主唱周晓鸥以乐队名义宣传遭索
- ·人大常委执法检查组建议修改老年人权
-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抵北京开始
- ·夫妻建数据库倒卖个人信息--中国国情
- ·公安部将在全国开展清剿火患行动遏制
- ·超市老板退货不成打伤送货员--中国国
- ·男子买小产权房被判无效 起诉房主讨
- ·北京职工获全国五一奖章将获万元奖金
- ·个税修正草案未表决 公众普遍认为300
- ·3辆公交车连环追尾致5名乘客受伤(图)
- ·上门女婿不愿离婚杀妻后自残(图)--中
相关链接
- ·北京地铁2号线因信号故障双向受阻--
- ·北京月底调整汽油标号 90号93号97号
- ·北京市主要网站斥巨资购买版权--中国
- ·北京多地为降低PM2.5加设检查岗查尾
- ·北京首发PM2.5日均值 专家称有利评价
- ·街道办主任微博与居民互动 处理房屋
- ·博士生以实验室研发情景剧 花500元自
- ·4岁女童被陌生男子强行抱走 路过老人
- ·女子6次谎称怀上孩子骗情人300万--中
- ·女孩与同性恋网友见面遭强制猥亵--中
- ·小伙手捧鲜花地铁求婚遭拒后昏厥(图)
- ·北京天坛祭天使用唯一指定用酒引争议
- ·疑犯在地铁关门瞬间抢走乘客手机--中
- ·北京站今日拆除临时售票处(图)--中国
- ·北大校长周其凤称中国教育很成功--中
入编邀请更多>>

2010版国情
媒体忆解放后进故宫修复厂专家:视文物如生命--中国国情手册
2011-0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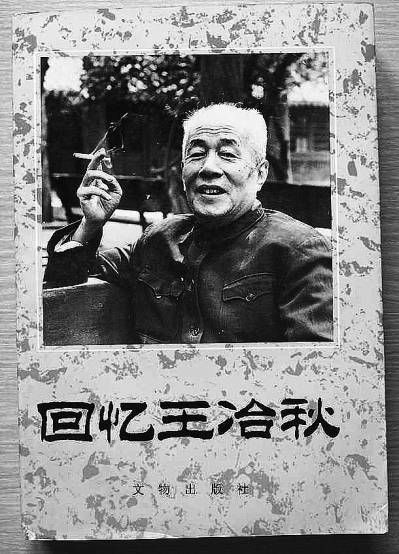

走进文物修复专家刘玉的书房,便可见故宫在这位75岁老人心目中的位置之重。一幅精心装裱的“皇帝之宝”宝玺印拓,被挂在书房最显眼的位置。
在故宫博物院(微博),许多技术一直是“单传”。作为著名书法篆刻家金禹民的传人,复制这方“皇帝之宝”宝玺,刘玉视为自己此生最引认为傲之作。
在故宫珍藏的“二十五宝玺”里,“皇帝之宝”是唯一一方木质宝玺,除4方传国宝玺外,它被列为21方日常公务宝玺之首,是真正意义上“宝不离身”的御物。从乾隆十三年钦定使用开端,至宣统末年进入紫禁城库房,它在完成自身使命的同时,也见证了一个王朝的覆灭。
1925年10月10日,当紫禁城有了新的名字“故宫博物院”时,这方宝玺带着自身177年的历史,成为顶级文物。它被复制,则是48年之后的事。当时,年近七旬的金禹民已半身不遂。完成复制任务,便成为他的单传弟子刘玉义不容辞和当仁不让之事。
不仅如此,从踏进故宫博物院开端,直至1998年,刘玉为故宫摹刻复制印章5000多方。如今,这些印章排列在一组柜子里,几乎挤满了故宫博物院摹画室的一面墙,其中包含印在故宫所藏《兰亭序》摹本上的148方印章,还有印在顾恺之《洛神赋》、韩滉《五牛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的印章。特别的身份,让老人成为当世唯一复制过帝王玺印、官印和历代书画家、珍藏家印章的人。
如今,提起解放落后入故宫博物院修复厂的那些修复专家,缄默寡言的刘玉是个绕不开的人。他在故宫的文物修复历史上占领着一个奇特的位置。
但是在老人自己看来,他在故宫里最大的收获,不是一门功底扎实的手艺,更不是一个象征着虚名浮利的位置,而是踏踏实实规规矩矩地做人做事之道。
视文物如性命的一代人
“我参与复制过数百件故宫书画顶级藏品,工作中没涌现过差错,也没听说过其他人出过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心中有‘文物胜于性命’的理念。”8月27日,在书房里接收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刘玉首先拿出的是两张已经发黄的稿纸,其中一张开头便写着这样的字句。
在鬓发皆白的老人身上,已经看不到55年前那个行色匆促的青年的影子。回想起故宫的经历,刘玉也不再是老伴和同事眼中那个“平时半天憋不出一句话的诚实人”,从他口中娓娓道出的往事栩栩如生。
1956年9月1日,刚刚从当时的北京三十三中高中毕业的刘玉,到故宫报到上班。对这个家庭成分为“地主”的京郊青年来说,能找到一份工作,已属万幸。他特地挑选学校开学的日子到单位报到。故宫于他,更像是一座新学校。
他的母校离故宫不远,学校组织“五一”、“十一”游行时,会路过天安门城楼,但20岁的刘玉从未进过故宫。因为当时故宫门票卖5分钱,作为中学生他无力承担。到故宫报到这天,他身上也只揣着一毛钱。
从午门绕到新华门,再绕到神武门后,刘玉第一次见到了故宫的内部面目。此前,这座精深的红墙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一无所知。
也是在这一年,28岁的蔡瑞芬服从组织部署,追随丈夫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工作。此前,这个上海市市立助产学校毕业的中专生,曾为即将奔赴抗美援朝前线的志愿军士兵检查身体,帮他们治疗血吸虫病。送走这些年青的战士,蔡瑞芬进入上海市卫生局工作。
她的一些同学或同事跟她一样随丈夫进京,但大都通过各种途径,留在了医疗系统。蔡瑞芬则没有,她后来成为故宫修复厂厂长。
“都是干革命工作嘛,在哪儿都一样。”今年83岁的蔡瑞芬笑着回想说。
她和丈夫是被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调入故宫工作的。吴仲超于1954年6月被从华东局副秘书长、党校副校长任上,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后来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期间,刘玉曾与吴仲超的外甥住同一宿舍。对方告知他,中央本来盘算将52岁的吴仲超从上海调至北京,到中央办公厅担任领导,但曾担任过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吴告知有关领导,自己喜好文物,自动要求到故宫工作。
在后人的记忆里,吴仲超担任院长后,除了在故宫内四处了解文物的状态,极其看重文物修复,还从故宫外四处招揽人才。
“没有一大量专家和业务骨干,故宫博物院是办不好的。”蔡瑞芬回想,吴仲超经常这样告知故宫的领导干部们。蔡瑞芬的丈夫在上海是吴仲超的部下,被他调到故宫担任古建队队长。
那时,故宫修复厂尚未成立,只有文物修整组。除了调来自己的老部下,吴仲超还从上海请来郑竹友、金仲鱼等专门临摹复制书画的人才,又从上海、苏州、杭州等地调来张跃选等一些裱画的名家。
对这些名家,吴仲超极为尊敬。“保护专家要像保护稀有动物熊猫一样。”蔡瑞芬记得,院长曾这样幽默地比方说。在那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修整组的人数从40多人增长到60多人,新增的20多人大都技术水平特殊高。
修整组办公地点在隆宗门右侧的西三所。在华丽堂皇的故宫里,这里感到有点偏僻。蔡瑞芬听说这里是失宠的前朝妃子待的地方,“有点儿像冷宫,但不完整是冷宫”。
然而在1960年,这里一点儿也不冷僻。在从社会上招募了众多名家之后,故宫博物院修复厂正式成立。
在刘玉拿出的另一张发黄的纸上,扼要写着修复厂的历史,还细心地写下了硬木桌椅、小器作、镶嵌、象牙雕刻、古铜、新铜、雕漆、彩漆、糊匣、钟表、裱画、摹画、书法篆刻和照相等14个行当。历史上还曾有珐琅和琢玉两个行当,因为不实用,存在了很短时间便被撤销。除了这些行当,他还写下了郑竹友、金仲鱼、金禹民等在文物界鼎鼎著名的师傅的名字。
正是在这些名家手里,一些受损严重的文物,性命得以延续。
1977年1月,唐代画家韩滉的《五牛图》被送到故宫修复厂。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颠沛流离,这幅传世名画当时已经千疮百孔、遍体霉斑,仅五牛身上大小洞浊便达数百处。吴仲超等人决定将挽救修复《五牛图》的任务交给裱画专家孙承枝师傅。
蔡瑞芬和刘玉等人记得,接到任务后,孙师傅有很长一段时间寝食难安,拿着放大镜重复查看,好不容易才精心制定出修复方案。经过淋洗脏污,画心洗、揭、刮、补、做局条、裁方、托心等步骤,接着补全画心破洞处的颜色,再经镶接、覆褙、砑光等,以宣和式撞边装裱成卷——工作几乎做得天衣无缝。后来他们才知道,仅仅为了揭除紧贴画心的一张贴纸,孙师傅便整整用了5天时间。
而在孙师傅潜心修复《五牛图》的同时,刘玉则忙于复制印在《五牛图》上的印章。
8个月后,吴仲超亲自带队的验收专家组,对孙承枝的修复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件性命垂危的顶级文物,就此重新焕发活力。
而在修复厂刚刚成立时,裱画专家杨文彬师傅便率领弟子们抢救了名贵文物卢棱伽《六尊者像》册的命运。卢棱伽是唐代“画圣”吴道子的弟子,这幅作品在故宫宫殿佛龛下被发现时,受潮发霉严重,几乎殃及每页。
杨文彬生性庄重、心细,且技术水平高,负责主修;残缺部分则由金仲鱼接笔、做旧。这件文物就这样起死回生。而故宫也在1961年经国务院批准,被定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只是这些常年临摹修复书画的师傅,虽然延续了文物的性命,他们自己的性命却因此受到伤害。因为长期用眼,他们中的不少人伤了眼睛,老一辈的师傅如此,晚一辈的刘玉也如此。蔡瑞芬虽然主要从事行政工作,但自从1962年被选拔为副厂长后,不得不开端了解各个行当的工作,她后来和刘玉一样得了青光眼。
“我们当时别的都不斟酌,‘文物第一’。”蔡瑞芬一边说,一边揉着自己的眼睛。
未曾学艺,先学做人
1963年,院长吴仲超把做木器行当的年青人刘玉叫到自己面前,告知他,根据革命工作须要,他有可能要改做书法篆刻行当。随后,院长把刘玉和另一个年青人带到摹画室唯一一位篆刻家金禹民师傅面前,说:“挑一个做徒弟吧。”
解放前,中国印坛有“南陈北金”之说,“金”便是金禹民。但此时吴仲超注意到,“北金”已经57岁,再过3年就要退休,故宫书法篆刻这行当,不能后继无人。同时,院长也注意到木器室27岁的小伙子刘玉性情内向,处事庄重。
金师傅没有多说,只是顺手给两个年青人每人一块寿山石,“刻完以后,交上来再说”。这一块寿山石,最终让刘玉成为故宫书画印章复制的唯一继承人。
随后,领导找刘玉谈话,“时间紧急,必需在一年后就投入工作”。对于之前没怎么接触书法篆刻的刘玉来说,“思想压力很大”。他开端到处寻找与篆刻有关的书,除了单位的材料室,中华书局、荣宝斋对面的庆云堂,他和同事刘炳森经常出入。
刘炳森在1963年进入修复厂摹画室工作,是修复厂的第一个大学生。除了一起逛书店研讨书法篆刻手艺,刘玉还曾和他一起到潭柘寺邻近,翻山越岭寻找治印的石料,经过几次踩点后,他们为故宫拉回了一吉普车治印的石料。
在这些年青人眼里,故宫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那时候人非常敬业,真的认为维护文物的性命就是保持自己的性命。”刘玉形容道。
当刘玉在荣宝斋对面出入时,荣宝斋的陈林斋和冯忠莲则来到故宫摹画室。根据当时的规定,故宫的文物不能出宫,他们奉荣宝斋之命到故宫临摹《清明上河图》。
两人只能隔着玻璃细心用放大镜看这幅顶级文物,然后贴着照相师傅所拍的黑白照片构图,再对比原件和照片,一点一点地临摹复制。从1962年开端,他们一直临摹了4年多时间,尚未摹完,但由于“文革”爆发,故宫闭馆,他们的临摹工作不得不中止。
已经被选拔为副厂长的蔡瑞芬被批评为“保皇派”,和刘玉、郑竹友等文物修复人员,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劳动。在阴雨连天的南方,刘玉和一些老师傅极不适应,但是还得经常戴着破草帽、披着黑塑料布或蓑衣,光着脚冒雨在稻田里劳动。
这一劳动进程和“文革”,让修复厂损失惨重。郑竹友的夫人在干校劳动期间逝世,郑竹友不久后也与世长辞。这个20多岁就以仿制和辨伪古画成名、曾令张大千惊讶的一代名家再也未能回到故宫。青铜器组组长古德旺倒是回到了故宫,但由于弄坏了手,只能在神武门看大门。至今还有不少人记得,不论是珐琅彩华表上掉了的双龙头,还是西四一座寺里被损毁的佛像,古德旺看着照片,不画图纸就能直接敲出原样。这当年是他的一大绝活儿。但是,当从神武门再次回到西三所,他只能无奈地看着那些残缺的青铜器文物,再也无法让它们在自己手里起死回生。
分享到: 欢迎发表评论我要评论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微博推举 | 今日微博热门(编辑:SN026)相关链接
- 北京地铁2号线因信号故障双向受阻--中国国情
- 北京月底调整汽油标号 90号93号97号汽油将取消--中国
- 北京市主要网站斥巨资购买版权--中国国情手册
- 北京多地为降低PM2.5加设检查岗查尾气超标车--中国国
- 北京首发PM2.5日均值 专家称有利评价空气质量--中国国
- 街道办主任微博与居民互动 处理房屋漏水违建等--中国
- 博士生以实验室研发情景剧 花500元自拍6集短剧--中国
- 4岁女童被陌生男子强行抱走 路过老人将其救下--中国国
- 女子6次谎称怀上孩子骗情人300万--中国国情
- 女孩与同性恋网友见面遭强制猥亵--中国国情网
- 小伙手捧鲜花地铁求婚遭拒后昏厥(图)--中国国情网
- 北京天坛祭天使用唯一指定用酒引争议--中国国情网
- 疑犯在地铁关门瞬间抢走乘客手机--中国国情手册
- 北京站今日拆除临时售票处(图)--中国国情手册












